日漸走遠的“寡婦村”重返銅缽村探尋30年的悲歡離合
想獲得更多廈門生活知識及商品優惠信息請點擊這里客服咨詢: 日漸走遠的“寡婦村”重返銅缽村探尋30年的悲歡離合" title="日漸走遠的“寡婦村”重返銅缽村探尋30年的悲歡離合" />
日漸走遠的“寡婦村”重返銅缽村探尋30年的悲歡離合" title="日漸走遠的“寡婦村”重返銅缽村探尋30年的悲歡離合" />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的銅缽村。圖/臺賽攝影師 林世澤
“妻在海峽西,夫在海峽東,日日盼夫不見夫,共望海峽水。”這曲曾經在東山民間流傳一時的歌謠,訴說了兩岸幾十年封鎖隔絕中東山多少分離夫妻漫長的守望,充滿悲涼與凄楚。1949年那一場“兵災”,一夜之間被抓走147名壯丁的銅缽村,至此,骨肉分離、悲歡離合的許許多多故事在這個飽含酸辛的“寡婦村”傳開了,而銅缽村的真名反而淡化了。
歌謠中這個曾經充滿冷感的村子,處在東山島的東北角,背負著“寡婦村”名號60多年。如今,再次走進村子,面對大大的水泥路時,反倒有一絲恍惚,這個原名“銅缽村”的村落,如今除去村邊觸目驚心的“寡婦村紀念館”之外,已經很難再找到有關“寡婦村”的任何痕跡。幾十年波瀾起伏的感情漸漸歸于沉寂,只能從一封封家書、一張張老照片找尋那段過往。
1987年,在知道臺灣開放居民回大陸探親后,銅缽村的寡婦吳阿銀、李阿葉、林春冬等在村口大榕樹下。

1987年,在知道臺灣開放居民回大陸探親后,銅缽村的寡婦吳阿銀、李阿葉、林春冬等在村口大榕樹下。
一夜之間被抓走147名壯丁
拐過一塊寫著“銅缽村”三個大字的石頭后,即為村落所在。夾道的花木葳蕤,綠樹隨風搖曳,清晨時分的銅缽村,雖然艷陽高照,可徜徉在村里,總伴隨著海風,透著一絲絲涼意。村民們三三兩兩地拽著漁具朝著海邊走去,彎彎曲曲的小路邊上,是高矮不一的典型閩南古厝、兩三層樓的小洋房,有小孩坐在門檻上遲疑地望著我們的鏡頭,從深深的庭院望進去,更多的是一圈一圈圍在一起,泡茶聊天的人們。
雞也不叫狗也不吠,懶洋洋地邁著外八字從我們身邊踱過,整個村子很悠閑、富足,跟印象中的銅缽村有很大的落差,感受不到絲毫的孤獨、凄涼。
在黃鎮國的帶領下,我們在懷鄉亭公園前停下了腳步。黃鎮國是土生土長的銅缽村人,今年75歲的他很有名,中央、省級的許多媒體都采訪過他,幾十年來,他一直在替村里的寡婦們寫家書到對岸,可以說是最了解這段歷史的人。
雖然叫懷鄉亭,可主角卻是其中那棵蔥蔥郁郁的老榕樹。眼前的榕樹,與平日里見到的散落在閩南各處的古榕,并無任何差別。只是在其腳下多了好多的大石頭,往昔它承載著重重的思念和遙望,寡婦們在榕樹邊翹首以望,祭香懷念的日子,畢竟漸漸遠去了。而今的它,安然回歸自然中的一株草木,揮揮手,歷史的煙云逐漸散去。
在閩南,像這樣有一定年歲的古榕,并不少見。不過用黃鎮國的話來說,這是一棵有故事的榕樹。黃鎮國說,過去古榕所在地,即為銅缽村村口,開放探親后,不少回來的老兵回來后,很多都是先找到了古榕,才找到了家。
68年前,古榕目睹了147名壯丁登上開往對岸的船,自此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銅缽村內百里無炊煙,榕樹下盡是淚眼模糊,翹首對岸的孤單背影。30年前,它又見證了兩岸開放探親后,那些將淚熬成糊再就著生活的清酒咽下去的苦命鴛鴦們,半世紀后再聚首后的不盡辛酸復雜滋味。而當日,除了榕樹上系著的褪去顏色的紅絲帶,地上還有散落的殘香。
時間回到1950年。東山的老年人都清楚地記得發生在60多年前的那一場大浩劫,東山島解放前夕,駐島的蔣介石軍隊敗退臺灣時,大肆抓丁擴充兵源,從島上抓走近5000個青壯年,銅缽村也難以幸免。5月10日凌晨2點左右,國民黨軍以清點常住戶口為名,把銅缽村里虛齡17歲以上55歲以下的男子全部集中在村里的黃氏宗祠前,強行將200來戶的銅缽村147名“適齡”壯丁擄到了前往臺灣的大船上,有的新婚燕爾,有的剛剛訂婚……頓時,一片悲傷籠罩了銅缽村,“三日不見炊煙”。至此,銅缽村一夜之間冒出91名事實上的寡婦,夜夜生悲,“寡婦村”之名不脛而走。
黃鎮國告訴記者,雖然其他村莊也有被抓的壯丁,有的被抓人數甚至比銅缽村還多,但只有銅缽村被稱作寡婦村,區別在于銅缽村是一夜之間全部被抓走的,整個村莊的情感深受重創。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黃鎮國就為寡婦們寫信。圖為他向記者展示臺胞黃建忠贈給的鋼筆。墻上右邊相片為黃建忠和“代筆功高,贈筆情長”的故事簡介。
寡婦村難覓寡婦
38年的分離,物換星移,扎紅頭繩的青年女子轉眼成了滿臉皺紋的老婦,盼瞎了眼,等白了發,有的等來的卻是丈夫早已去世的消息。上世紀90年代,每年都有老兵回到這里探親,但這些年,他們都老了,走不動了,更多的已經離開了。
除去村邊觸目驚心的“寡婦村紀念館”之外,已經很難再找到有關“寡婦村”的任何痕跡,只能透過一張張泛黃的照片、一封封往返兩岸的信件來鉤沉那段辛酸的過往,原寡婦村紀念館館長的黃鎮國對此再熟悉不過。事實上,他本身也是受害者親屬。1950年,黃鎮國的父親剛去世不久,而他還在母親的胎中。可他的堂哥、表哥都沒能幸免被抓壯丁。堂哥黃亞慶是被抓兵去臺的已婚者之一,堂嫂沈錦菊和村里其他失去丈夫的婦人們,開始了漫長的守活寡、盼親人的痛苦生涯,撐起男人拋下的重擔,耕種田園,孝敬公婆,撫養子女。
他告訴記者,寡婦村紀念館講述的是寡婦們的故事,而非他們丈夫的故事。
38年的風風雨雨中,黃鎮國訴說著這些等待的寡婦三種不同命運,有的是一別成永別的,他指著館內一張張祭拜的照片告訴記者,這些都是每年清明節回鄉祭拜死去親人的鏡頭;一種是妻子尚在,但對方卻在臺灣有家庭的,每年他們會回家探親,這種情況所占比例較高;最后一種是最圓滿的,也就是葉落歸根,老兵回來便定居下來,在這里跟妻子度過晚年。記者在櫥窗內,看到了這令人驚喜的、重聚的一幕幕,包括林阿玉與丈夫黃韻奇、陳巧云與丈夫黃阿嵩、林水鮮與丈夫蔡秋昌、吳阿銀與丈夫謝老王、林美桃與丈夫黃拱成等。1984年,黃文克從海外輾轉回到了銅缽村老家,成了村里首個離臺回鄉老兵。黃鎮國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對妻子、兒女說:“那些年我想家想得都快要發瘋了”。
黃鎮國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初,雖然陸陸續續地有老兵回鄉,但一直到了1987年后,返鄉探親潮才達到了高峰。
1987年10月,臺灣當局決定開放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終于被打破。同年12月10日,銅缽村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幕。這一天,8名當年的“壯丁”回到了家鄉。黃鎮國的堂哥黃亞慶也在1990年回到銅缽村探親,最后回鄉定居,和沈錦菊享受天倫之樂。

黃鎮國正在為去臺人員眷屬林阿嬌代筆寫信給臺灣的親人。
為“寡婦”寫信易寄信難
時間如水,寡婦的故事在黃鎮國的筆下,在他一封封的信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可以說,黃鎮國用手中的筆呼喚著一個又一個漂泊的游子踏上了回家的路,讓一對對劫后“鴛鴦”重團圓,骨肉重相聚。
從十二三歲開始,黃鎮國便開始替村里不識字的“寡婦”們給臺灣的親人寫信。他第一次代筆,是幫堂嫂沈錦菊寫給堂哥黃亞慶。他堂嫂說了兩句就哭了。黃鎮國從她眼淚中就知道信該怎么寫了。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他給堂嫂代筆,書信都是通過在新加坡的祖母轉寄,這是當時兩岸通信的慣用路徑。
寫信容易,寄信難。東山是閩南著名僑鄉,僅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間,就有3萬多人因生活所迫去了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賣苦力謀生。過去,這些幫“寡婦”們寫的書信要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找到親戚或朋友,再將信件從東山縣寄到這些國家,然后由這些國家的親戚或朋友換上一個新信封,再轉寄到臺灣去,托人查找到收信人。臺胞寄信到家鄉也頗費周折。常常一封信要輾轉好幾個月才能到達收信人手里。1987年前夕,第一次回到銅缽村的黃韻奇,一人帶了100多封老兵的信回來,除了東山本地的,還有周邊縣的,比如詔安、云霄的。

臺屬林阿鮮(左)通過黃鎮國近40年的代筆寫信,終于與丈夫蔡秋昌(右)團聚了。
東山縣委宣傳部原副部長謝漢杰,長期報道寡婦村故事,他告訴記者,1963年,銅缽村人收到第一封經第三地輾轉而來的臺灣來信。從此,去臺人員的親屬們紛紛試著想給彼岸生死未卜的親人寫信聯絡。“要寫信的人太多了,要把信寫好,就得用心寫。”很多時候,找黃鎮國寫信的鄉親都排起了隊。多少次,他端起飯碗剛想吃飯,或者出外辦事深夜回來,就有人拿著紙筆找上門來,他總是笑臉相迎,熱情相待,當場鋪開紙就寫起信來。黃鎮國坦言,有時候高峰期,一天寫個四五封。村里“寡婦” 林阿鮮的丈夫蔡秋昌被抓兵去臺灣,黃鎮國30多年義務為她寫信寄去臺灣,1991年她丈夫蔡秋昌回來定居。每年“臺南榮民院”來往書信回復及寄來的“養老金”等手續的辦理全靠他的熱心幫助。
黃鎮國告訴記者,信的內容很簡單,不過不同階段內容存在差異。1987年11月,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并于次年同意臺灣民眾給大陸親友的信件可以經香港郵局轉寄大陸,黃鎮國更加忙碌了,而且代筆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開放前,代筆基本都是報平安、訴離情;開放后,代筆的主要內容變成幫助提供資料,協助一些臺胞申請回來探親、定居。
黃鎮國告訴記者,剛走過的大榕樹后那層三層樓高的小洋房,那是已逝寡婦陳巧云的家,10多年前她曾上過央視的講述欄目,彼時自己在旁邊作陪并充當翻譯。當年的她,在村子里,不僅會唱歌,還會替從關帝廟回來的善男信女們解簽。陳巧云的丈夫黃阿嵩被抓時,丟下一個6歲的女兒、一個2歲的兒子,全靠她瘦弱的肩膀承擔起破碎的家庭,她子女早已成家立業。1988年10月,黃阿嵩第一次回到老家,之后每年都回家,因為家里都有自己惟一的妻子和孩子。終于等到了那一天,1992年,黃阿嵩辦了回老家定居的手續,從此一家子便生活在一起,一直到過世。

懷鄉亭里的大榕樹,曾經是銅缽村寡婦們翹首以盼丈夫歸來的地方,承載了重重的思念和遙望。
被一首詩追回的老兵
幾百封、上千封,三四十年來,黃鎮國為寡婦們寫過無數封的信,具體多少,他不記得,也沒算過。透過這些信,老兵們紛紛踏上了回家路,也留下不少遺憾,比如黃寶蘭始終沒能等到兒子黃建忠回來。
在紀念館二樓展廳,擺放著一支鋼筆,上面刻著“知書達理, 代筆功高”,臺灣黃建忠敬贈等字,說的便是黃寶蘭這對母子的故事。黃鎮國坦言,這也是代筆過程中最難忘的。
黃建忠是黃阿九和黃寶蘭的獨子,被抓去臺灣時年僅17歲,在20年毫無音信的情況下,夫妻便將原本為兒子定親的童養媳黃亞卿,找了一位入贅的女婿,來延續黃家香火,而黃建忠也在臺灣組建了家庭。上世紀60年代中期,其父母親多次請黃鎮國代寫書信,經外國親人輾轉寄給臺灣的兒子。有一次,黃建忠從新加坡輾轉寄來一封信和一張照片,背后寫了“顧影自憐”四字,其父母親非常高興。但在這之后,雖然還有幾次書信往來,不過好景不長,在新加坡為黃建忠代轉書信的親人病逝了,黃建忠從此中斷了與大陸的聯系。
1975年秋天,黃建忠的父親黃阿九老人在不知兒子生死的絕望中去世。1980年底,黃寶蘭一病不起。臨終前,她將黃鎮國叫到病床前,請他給兒子寫封信。黃鎮國說,這封信其實是遺書;她說:兒啊,我等你幾十年了,這次病重,也許你沒收到我信時,我已經死了。但我死不瞑目。別忘了,兩岸太平時候帶妻兒回家,到墳前給我和你父親燒香紙,讓我看看你們……”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封信,黃建忠并沒收到。一直到1990年,幾年來,老兵都陸續回來,卻唯獨不見黃建忠,中秋節那晚,黃鎮國百感交集,他既為已經聯系上的家庭高興,更為尚未團圓的人們焦急,又提起筆來,代黃建忠妹妹寫一封信,信中除了告訴黃建忠:自己就是代筆之人外,還隨信寄上一首含意深蓄的新古體詩----《中秋即情----寄臺宗兄》:“歲月無情幾度秋月圓人缺何時休月色溶溶何時醉何時良宵醉悠悠誰家月下天倫樂何人庭中獨自愁天下風云總難測,趁峽浪平好行舟!

如今,銅缽村的玉二媽,成為繼老兵后,勾連村子與臺灣之間最重要的交流渠道。300多年來,玉二媽香火在臺灣深深扎根并不斷繁衍,臺灣各地玉二媽廟的信眾,也時常回來銅缽村的祖廟進香祭拜。圖/臺賽攝影師 林世澤
這封信通過其他臺胞轉到黃建忠的手里。不久,黃鎮國收到黃建忠的來信,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2個多月后,黃建忠終于回來了,他帶上“四色”禮品,在妹妹黃亞卿的陪同下登門拜訪黃鎮國。一見面,他就對黃鎮國說:“兄弟,我被你的那首詩追回來了。”此后,黃建忠多次返鄉為父母掃墓。去年8月,黃鎮國去臺灣旅游期間,還見到了家住臺南市,年已82歲的黃建忠。
悲歡離合,黃鎮國動情地說,歲月的流逝無情地帶走了兩岸的許多老人,當年的91名“寡婦”,現在健在的只有3人,回村定居的19位老兵都已去世;留在臺灣的那些老兵,目前健在的剩下4人,黃建忠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
誠如謝漢杰所言,寡婦村的悲劇已成為歷史。如今的銅缽村一片祥和。銅缽村房屋建筑面積比1950年擴大了20多倍,全村范圍也比過去擴大了好多。但見銅缽村四周與銅陵鎮新城區、東山口岸聯檢機構、馬鑾灣別墅群相連,傍晚時分,這里人氣高漲。
由于老兵年紀大,這些年來走動少了,但長期的頻繁互動,卻也促成了兩地的聯姻。據黃鎮國介紹,有五六個銅缽村女兒嫁到了臺灣。事實上,一直以來,銅缽村與臺灣便有很深淵源,距離高雄僅有110海里,跟金門就更近了,過去海上捕魚,兩岸漁民間就常有互動。
事實上,早在明末清初,40多名銅缽村青壯年隨鄭成功收復臺灣,并將銅缽玉二媽祖廟的“二娘娘”奉上戰船作為保護神。據說,海上戰船交鋒時,其它戰船皆有毀損傷亡,唯獨有“二娘娘”金身的戰船上,銅缽將士全部幸免,于是將士們都對“二娘娘”顯靈助力的說法深信不疑。
為了紀念“二娘娘”抗御外侮、收復國土的“神功”,激勵并讓子孫后代永遠銘記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村民們決定兩尊并列供奉,并把隨鄭成功出征并返回的一尊稱為“大媽”,后雕塑的一尊稱為“二媽”。這也成為如今全國各寺廟中獨一無二的文化。300多年來,玉二媽香火在臺灣深深扎根并不斷繁衍,除了臺南祖廟,還有嘉義、臺北、臺中、基隆、桃園、高雄等地“玉二媽”廟12宮,信眾遍布臺灣達數百萬人。
文/《臺海》雜志記者 盧燕 實習生/黃海綿
通訊員/謝漢杰 圖/謝漢杰
廈門日報社微信矩陣 | ||||||
昵稱 | 微信號 | 昵稱 | 微信號 | |||
廈門日報 | xiamenribao | 廈門招考 | xiamenzhaokao | |||
廈門晚報 | xmwb597 | 海峽生活報 | lifeweekly0592 | |||
海西晨報 | haixichenbao | 臺海雜志 | taihaizazhi | |||
廈門網 | xmnn-cn | 遇見婚戀網 | yujianw520 | |||
| ||||||

本資訊信息是來自 逛鷺島 小編 通過網絡收集而來的關于廈門最新最熱門的本地資訊。
您若也有需要分享的可以直接在我們網站上分享你的內容,讓大家都知道。
版權聲明,本活動信息隸屬網絡收集而來若有侵權請聯系我們,我們將及時清除信息。
獲得更多廈門生活知識及商品優惠信息請聯系我們:
關注我們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眾號


想獲得更多廈門生活知識及商品優惠信息請點擊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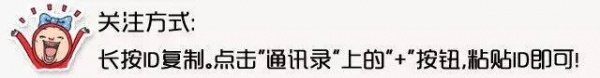


你設置的聯系郵箱是*: (當有人給你留言回復之時,聯系郵箱可以及時通知你)
我們建議你填寫正確的郵箱地址,如果你之前填寫郵箱地址是錯誤的可以通過 【修改資料】 來重新設置